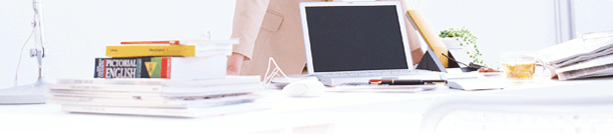地缘政治之土耳其
由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不出意外的话将占据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各个媒体的重要版面。而在人们把关注点放在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军事、经济领域的数据对比的同时,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任何一国的对外政策,本质上都是其国内政治的延生产物。
可以说,国际事务其实都是:三分外交,七分内政。而要看清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最好的方式则是回顾总结其历史,从“基本盘”入手。
由来已久的结构性问题
凡事欲知其所往,必先知其所来,对于土耳其来说自然也不例外。
一切还要推回到奥斯曼帝国时期: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新帝国就此诞生了。她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只脚踏在亚洲,另一只脚则踏在欧洲,这便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此之后帝国的版图日愈扩大,最终在16世纪步入巅峰,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奥斯曼帝国在当时完全占据了“世界岛”的中心地带,这最终迫使西欧放弃了与东方的陆上商路,从而歪打正着的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而在自苏莱曼一世去世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开始逐步走上了下坡路。1517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从此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十七至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交战中迭遭失败,势力进一步转衰——九次俄土战争几无胜绩,失地千里。随着国运的衰败,至十九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后独立,英、法、俄、奥也相继开始争夺其领土,阿拉伯半岛上各行省的离心力也开始增强……
在衰落的表征之下,隐患的则是奥斯曼帝国一直以来的“结构性”问题。某种程度上说,奥斯曼帝国与中国的明、清两代帝国存在着类似的困局。奥斯曼帝国自立国之初,就奉行政教合一的机制,苏丹也是帝国的哈里发(宗教领袖),伊斯兰教成为把帝国治下不同民族的民众统一起来的纽带。
这种体制,在保持帝国统一的同时,也赋予了教士阶层以极大的权力。日久天长,便形成了居于自身利益的宗教保守派。这个阶层将君主与民众彻底的割裂开来,使得国家治权分散、中央财政弱化,在面对新兴崛起的西方国家时,自然会落了下风,这种情形类似明末的东林党对皇权的架空。随着与西方国家接触的增多,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出现了新兴的精英阶层,他们主张参照西方进行改革,这一点与同一时期东方的清帝国以及日本非常类似,而宗教保守势力也同样对此进行了空气严苛的打压。
而所不同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宗教保守阶层其实更接近底层社会,新兴精英则主要集中于西化的知识分子和新军中的军官阶层。这样一来,主张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新兴改革派就始终存在一个问题——不接地气。
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的微妙转变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中东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不止土耳其,后来走上相对世俗化改革道路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他们的变革过程其实都大同小异,都是由军官团主导革命,之后由军方主政,通过比较强硬的手段来压制宗教保守派,从而实现国家世俗化。
凯末尔正是这一“经典”模式的开创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面提到的奥斯曼帝国的结构性问题,在宗教保守势力的掣肘下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在英法两国的联合进攻之下,帝国最终分崩离析。而对土耳其民族来说,这种过程也可以称之为“否极泰来”。伴随着帝国的崩溃,苏丹和宗教保守势力都遭遇到了重创,由凯末尔领导的新军军官团得以崛起,于是有了凯末尔革命与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1931年4月,由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正式提出“六大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大众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改革主义。此后“六大原”于1937年被写入土耳其宪法,其实质即在于通过世俗化,最终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
前面说到:相对于军官团,事实上宗教力量与底层民众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进世俗化的过程其实是相当酷烈的,正是这种对宗教集团的强力打压,为后来土耳其的变局埋下了伏笔。
在完成国内整肃的同时,土耳其在军方的领导下开始迅速向西方靠拢。土耳其地跨欧亚,掌握着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成了土耳其“脱亚入欧”战略最大的本钱——1948年土耳其加入经合组织;1949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50年为了表示自己向西方靠拢的决心,土耳其参加“联合国军”出兵朝鲜;1952年正式加入北约,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起因真是美国在土耳其部署针对苏联的中程导弹;1963年欧共体与土耳其签署了接受土为“欧共体联系成员国”的《安卡拉条约》,条约规定在经过17年的过渡期后,可以考虑土耳其正式入盟。
而让土耳其新兴精英没有料想到的是,正是他们所最求的“脱亚入欧”导致了自己最终被边缘化,进而导致土耳其国内出现“逆世俗化”。凯末尔为土耳其设计的政治体制比较特殊,他并没有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军政府【凯末尔以法律的形式严禁现役军人参政】,而是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政府,而其特殊之处在于,土耳其军方一直在“监督民主”。更直白点说,为了脱亚入欧,土耳其必须要搞一套与西方社会匹配的政治体制,但自奥斯曼时代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军方必须时不时施加一些“外力”,才能保证土耳其不至于脱离世俗化的轨道,而最激烈的方式,就是政变。自共和国建立至今,土耳其军方先后发动过四次政变,最近的一次是在1997年。
当然,站在第三方角度来说,对此你也说不出个对错,只能说存在即有他的道理。1950年曼德列斯领导下的民主党上台,之后立刻对议会进行大清洗,军人出身的议员比例从1/2直降到1/25,随后宗教保守主义开始重新得势,新政府对上街抗议的青年学生采取严厉镇压,最终导致5人死亡,正是这次事件导致1960年土军方第一次政变。
真正让土耳其军方感觉到压力的,是西欧国家的指责。出于迫切希望加入欧共体(欧盟)的诉求,土军方对西欧国家的态度一直非常看重。而在欧洲左翼政治力量影响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西欧国家才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土耳其军方屡屡施压。1982年,欧洲议会甚至通过决议,暂停执行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以“惩罚”土军方在1980年发动的政变。
外部的压力导致土耳其军方对土国内的政局控制力开始下降,由此导致了颇为讽刺的一幕:西欧施压→土军方退让→世俗化力量式微→宗教力量做大→欧洲新移民宗教色彩越来越浓→欧洲族群矛盾加剧
而从土耳其内部来说,新兴精英阶层“不接地气”的问题始终存在,这直接影响到了最终国民的经济利益分配。在靠近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与内陆的农村乡镇,你会看到两个“土耳其”,一个充满了现代化气息,一个则贫困保守,而后一个在人看上则占了多数。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西方对土耳其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这一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出来。而正是这一外一内两层因素,构成了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上台。
与之前的套路差不多,正发党上台之后,随即以铁腕手段对土军方、情报及司法系统进行了一次严苛的清洗。而这一次,土军方或者说是世俗派在内外压力之下,已无法像上一次那样重新翻盘。
埃尔多安的困局
清楚了土耳其的这段历史,也就很容易看出来这样一个问题,如今最令埃尔多安头疼的恐怕不是普京,也不是库尔德工人党,而是土耳其自身。
正发党上台,带有明显的双重色彩,其一是强调宗教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其二则是民族主义。
凯末尔建立共和国之后,亟需在意识形态方面找到一个宗教的“替代品”,于是民族主义亦或说是“泛突厥主义”被祭了出来。从遗传性角度说,现代土耳其人的祖先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与中亚、东亚的民族并无血缘关系。但是政治需要依然使得大量的“历史”被“制造”了出来,需要说的是,这一举动使得相关国家至今依旧深受其害。在共和国进入稳定运行之后,土军方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开始逐渐冷淡,甚至予以过打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泛突厥主义者最终也成了正发党的支持者。
这两层色彩,使得埃尔多安的执政风格异常鲜明:内对趋于保守主义,强调宗教传统;对外则极富攻击性,不仅是针对俄罗斯,确切的说,对几个主要大国而言,埃尔多安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领导人。一直以来,土耳其与希腊的各种摩擦就没有断过,在美军占领伊拉克期间,由于美国会重提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埃尔多安一怒之下关闭了美国途径土耳其的后勤补给通道,一度将驻伊美军置于险境。
然而土耳其此前的强硬表现是有前提的:无论是对希腊还是对美国,无论土耳其如何强硬,最终的冲突烈度始终都只会维系在斗而不破的范畴,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体系之下。因为埃尔多安可以非常安全得获得来自底层的支持。
但这一次不同,土耳其和俄罗斯可能的冲突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埃尔多安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局之下:如果对俄罗斯态度软化,那么此前被一次次“胜利”激发起了的高涨民意,就可能直接吞噬掉这个“服软”的总统,即便后来者依然从正发党内产生,也还得继续面对这个问题;如果继续保持强硬,那么就必须做认真准备,那么就必须倚重于军方,而既然有求于人,那么自然就要把之前政治斗争的“成果”至少重新吐出来一部分。
而相对应的,对普京来说,俄罗斯显然没有和土耳其大打的必要和理由。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维持一种长时间低烈度的对抗局面——既让土耳其能感觉到压力,又不至于让这种压力转化为埃尔多安可以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
电话:010-80522028 传真:010-8052202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观音堂文化大道一期南花园村168号2号展厅25号
版权所有:北京思得乐图书有限公司 京ICP备20013354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131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131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