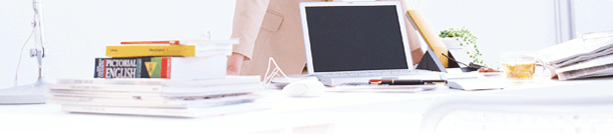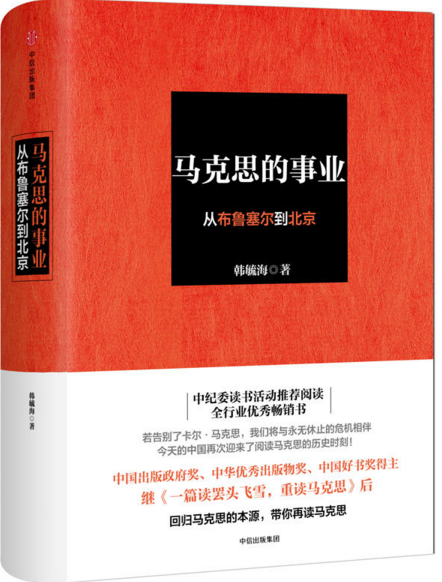序 言
这世上的书已经太多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的书?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规定动作”,那么,最自然的回答便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一个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词,但丁对此的著名定义是:博学深思是重要的,不过,单纯依靠思考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语言、文笔、画笔、凿子等把它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科学。
就是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众所周知,中国有历史上最完善的读书人选拔制度,有无数博学善思的学者,而欧洲最著名的大学皆是中世纪的产物,牛津、剑桥、博洛尼亚等著名学府都有教会背景,但是,正如欧洲中世纪的教士一样,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特殊阶层,一旦进入这个阶层,便脱离了劳动,更视“动手”为贱业。脑与手的分离—这便是现代科学不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和传统中国的根本原因。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佛罗伦萨(可直译为“鲜花盛开的地方”)这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艺术家与裱糊匠却没有什么不同,理发师与医生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佛罗伦萨人相信:只有当脚掌证实了心脏、思想与手的劳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开始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被但丁等人称为“科学”。
事实上,现代文化就起源于脑与手的结合,而这也正是现代文化与一切“旧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士大夫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现代文化的实质,无非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正由此而产生。现代文化的创造者是工匠,他们便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前身—这就是E. P. 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揭示出的历史事实。
然而,这种对“文化”的理解是如此有悖于人们的传统与积习,因为它与旧势力对“文化”的理解如此相悖,以至在某些人看来,正是这种散发着劳动和“动手”的寒酸与汗酸味道的文化、正是这种把“文化”和“下等人”联系起来的努力,严重玷污了那种充满了香水与“书香”味道的文化,亵渎了高尚的、纯粹的文化。于是,对于“文化”的这种崭新理解,从其产生的那一天,就对“纯文化”“纯精神”“纯文学”构成了挑战。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资产阶级文化不过是基督教文化的变种,它认为“身体”、手和脚是肮脏的,纯洁干净的只有“心灵”和“脑袋”。而让–保罗·萨特在《肮脏的手》中则这样讽刺说:
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什么也不干的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个手肘贴着身体,戴着手套。而我的手是肮脏的。我把它们伸到血污和大粪里去,所以它们一直脏到了臂肘上。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你可以天真无邪地掌权吗?
毫无疑问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代表着脑与手的结合,真正显示着现代文化波澜壮阔的伟大力量的,正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笑谈过这样的悖论:资产阶级文化中充满了上帝的爱、法律的尊严、纯洁的说教,但是,资产阶级的行动,却是由欺诈、卑鄙、阴谋诡计和残酷的镇压构成;而与之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文化中尽管散发着劳动者挥汗如雨的酸臭、洋溢着奴隶对于革命暴力的呼唤、赞美着革命者对于淋漓鲜血的正视,但是,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却是堂堂正正、大公无私、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行动。
尤为震撼的是:当马克思说到“动手”的时候,他所说的“动手”并不仅是指劳动,还有“革命”和“人民专政”: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他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合集》)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摘自《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与纯学术的说教毫无关系。“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在这种科学、这种文化中,不仅充斥着劳动的汗酸味,而且还布满了火药的气息。
因此,阅读马克思的书,既不会使你感到舒服,更不会使你升官发财,当然,这种科学、这种文化更与廉价的快乐无关。伊壁鸠鲁曾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快乐,而古往今来,很
多人是他的信徒,于是,他们读养生、健身、旅游、性爱、游戏、美食和赚钱方面的书,以为这样的书能使他们快乐。但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却调侃说,实验已经证明,快乐不过是内分泌和神经网络的运动,为了追求快乐,最直接的办法是去嗑药,而不是读书。某位号称“无知者无畏”的作家曾经说过,不读书我们一样快乐,没准儿会更加快乐—而他
很可能是对的。
我想,人们读书,一定是希望解决一些使自己感到苦恼的问题。因此,如果书籍不能给我们带来震惊、带来惊奇般的收获,如果书籍不能告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并挑战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知的“常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呢?一般的读者也许知道马克思出身于快乐、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且有一半荷兰血统,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的姨妈索菲亚和姨夫利奥·菲利普联手创办了著名的荷兰飞利浦公司。
而当你知道了这些之后,一定会追问:作为一个如此快乐的富二代,马克思为什么会成为为了世界无产阶级而痛心疾首的伟大导师呢?
马克思的故事和事业与“快乐”无关,却与马克思对于“幸福”的理解有关。实际上,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天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一样,只是把伊壁鸠鲁的名言稍作修改,即把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快乐”,改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
边沁说过:所谓最大幸福原则,就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世上最持久的幸福,就是使个人的幸福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协调起来的努力。
边沁还说:快乐与快感是动物也有的,但“快乐的猪”与高尚的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实际上,“幸福”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在他17 岁时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阐释的主题: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马克思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与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意义的理解,有着微妙却具有天壤之别的差异,因为在后者那里,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追求“快乐”的职业,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则是为人类谋“幸福”的事业。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即使卡尔·马克思博士今天还活在世上,这位《资本论》的伟大作者,仍旧不可能在我所在的“世界一流学科”谋一份教职,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对于“知识”和“幸福”的理解,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截然不同。
每当想起马克思的事业,每当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猪的快乐”与“人的幸福”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小学课本上的叶挺的《囚歌》,想起那些革命者对于幸福的理解: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 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鲁迅说“救救孩子”,而我只是不知道,像马克思17 岁时的那篇作文一样,叶挺的诗篇,是否还幸存在今天的小学课本里。
我们为什么要读马克思?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关怀全人类的命运,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能够感到自己与人类“共命运”—“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鄙视这样的无聊笑谈:“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到死了钱还没花了。”恰恰相反—正如康德所说,作为小人物,我们既在为自己的衣食而斗争,同时,也在情不自禁地在为后人、为他人而工作。
而这就是人的“类本质”,所谓“情不自禁”,“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却这样做了”。康德说:正是基于这一点,“每个人是必死的,但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知识、“文化”与下等人和劳动结合起来,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幸福结合起来。阅读马克思的理由有很多,但我以为这两条是最基本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学问,都通向马克思,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思想,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马克思逝世10 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而马克思
诞辰100 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报到——正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的思想便点燃了无路可走的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主义便成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火炬,马克思主义便与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要了解西方,需要懂得马克思,而西方人和全世界要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更需要懂得马克思。马克思的学说是如此博大精深,我们阅读并学习马克思,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万事开头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键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区别。
而世界上最难的问题,恰恰就是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辩证法?而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古希腊思想对世界本源的思考,包括两个部分: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把世界的本源理解为原子及其运动,形而上学则把世界的本源理解为数以及计算和预测——因此,形而上学也直译为“物理学之外”。
将命运归于数和“定数”,还是归于矛盾、运动与斗争?这既是一个宇宙观的问题,更关乎对于政治的理解,实际上,它也关乎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希腊城邦的命运。
所谓辩证法,不仅揭示了物质世界的运动,它也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也被称为“助产术”,即启发、帮助公民们把自己的话讲出来的方法。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就是古希腊城邦公民政治的基础。
但是,在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却被理解为“否定之否定”的教条,即在思想上否定、在现实中肯定(现实秩序)的庸人哲学。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它的核心,就是启发、帮助无产阶级——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他们的声音:“让人民说话,天不会塌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就是无产阶级实践力量的“助产术”,它最终凝结为波澜壮阔的《共产党宣言》。
黑格尔有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这句话的意思是:形而上学是在古希腊城邦政治衰败时(黄昏时刻)崛起的。这意味着,随着古希腊城邦的衰落,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代替了公民政治,也代替了公民政治的基础——辩证法;这也意味着,从那时起,在古希腊城邦,“哲学家”对思想的垄断,代替了生产与战斗着的公民的呼声。
在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古希腊城邦的沦陷,既肇始于哲学家的掌权与兴起、从事战斗与生产的公民的消失,更在于形而上学以数字的计算和逻辑的推演代替了自然哲学关于原子运动的学说。
马克思23 岁时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其目标与抱负,就是要恢复、发掘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并以此批判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篇极具开创性的文献,其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原子运动有两种必然性——互相吸引与垂直运动,而这两种运动互相作用的结果,则是原子运动不是直线运动,而是矛盾、对抗造成的“偏斜运动”。
正是以此为起点,马克思接续并发展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发展了自然哲学描述物质世界的辩证法。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通过继承康德“仰望星空”(星云爆炸)的视野,把辩证法由静力学的时代引向热力学的时代,从而把自然哲学锻造为唯物辩证法。
与形而上学不同,辩证法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世界的逻辑呈现,而在于宇宙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着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
只有了解古希腊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才能了解马克思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才能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只有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才能懂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西方哲学中,矛盾是对称、对等的,正如有正即有负,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而在毛泽东那里,矛盾是不对称、不对等、不均衡的,因此,就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有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就有其之间的对立转化。毛泽东曾说:小是大变来的,弱的一方,可以打败和战胜强的一方,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键,就是要善于掌握这种矛盾对立转化的规律和不平衡性。毛泽东对于辩证法的丰富与发展,集中体现为他独创性的矛盾学说,而这一学说,则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锻造出来的,因此被称为“血的哲学”。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均衡、不对称的思想,也深刻地启发了钱学森、丁肇中、屠呦呦等伟大的自然科学家。
人的正确认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马克思率先指出:所谓正确认识,不是对宇宙间“唯一规律”和“必然性”的沉思——那便是宗教的,或曰形而上学认识论,人的正确认识,来自包纳他人的视野,倾听他人的声音——特别是世界上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无产者和劳动者的声音。这种被马克思发展了的苏格拉底辩证法,又被毛泽东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实践”。
因此,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实践论》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马克思是极为高深的学者,我们阅读马克思所遭遇的最大困难,便在于马克思的著作是极为抽象的。但是,故作高深正是马克思所最为鄙视的,马克思著作的那种高度抽象性,绝不是马克思刻意为之,而是由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本身的高度抽象性决定的——把握这一点,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
希腊城邦的沦陷,既肇始于哲学家的掌权与兴起、从事战斗与生产的公民的消失,更在于形而上学以数字的计算和逻辑的推演代替了自然哲学关于原子运动的学说。
马克思23 岁时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其目标与抱负,就是要恢复、发掘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并以此批判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篇极具开创性的文献,其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原子运动有两种必然性——互相吸引与垂直运动,而这两种运动互相作用的结果,则是原子运动不是直线运动,而是矛盾、对抗造成的“偏斜运动”。正是以此为起点,马克思接续并发展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发展了自然哲学描述物质世界的辩证法。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通过继承康德“仰望星空”(星云爆炸)的视野,把辩证法由静力学的时代引向热力学的时代,从而把自然哲学锻造为唯物辩证法。
与形而上学不同,辩证法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世界的逻辑呈现,而在于宇宙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着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
电话:010-80522028 传真:010-8052202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观音堂文化大道一期南花园村168号2号展厅25号
版权所有:北京思得乐图书有限公司 京ICP备20013354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131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131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