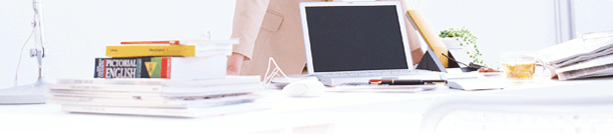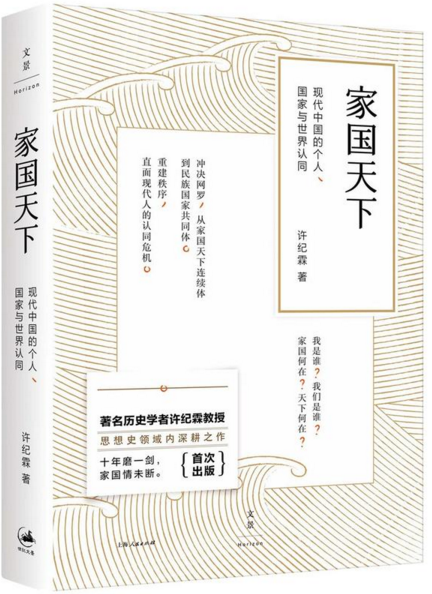新天下主义与中国的内外秩序
21 世纪影响世界最大的事件,可能是中国的崛起。但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扩大,中国的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却出现了严峻的紧张局势。在国内,边疆所发生的民族与宗教冲突没有解决,甚至出现了极端的分离主义和恐怖活动。在东亚,中国的崛起让周边有些国家惴惴不安,东海、南海的海岛之争令东亚上空战争的乌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危险。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都空前高涨,呈相互刺激之势。犹如19 世纪的欧洲,局部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危机的脚步临近家门,我们有化解危机的方案吗?治标的国策固然可以开列一张清单,但重要的乃是根除危机之本。这一本源不是别的,正是自19 世纪末引入中国的民族国家至上意识,这一意识如今已经成为社会从上至下的宰制性思维。民族主义本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然而一旦成为君临天下的最高价值,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就像曾经在欧洲发生过的世界大战一样。
真正的治本之方,在于一种与民族国家意识对冲的思维。这一思维,我称之为“新天下主义”,一种来自古代传统,又重新加以现代性解释的轴心文明智慧。
一、“天下主义”的普世性价值
何谓“天下主义”?在中国传统之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文明秩序,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国,“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作为价值体的天下,乃是一套文明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国不过是王朝的权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秩序,不仅适用于一朝一国,而且是永恒的、绝对的和普世的,国家可亡,但天下不能亡,否则将人人相食,成为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
中国的文明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天下的价值是普世的、人类主义的,而不是特殊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民族或国家的。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古代世界的轴心文明,就像基督教、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也是以全人类的普世关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以人类的价值来自我衡量的。当近代中国从欧洲引入民族主义之后,中国人的胸怀从此狭隘了许多,文明也因此而萎缩,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天下气魄,矮化为“那是西方的、这是中国的”小家子气。
固然,古代中国人除了讲天下,还讲“夷夏之辨”,然而,古代的夷夏,与今天挂在极端民族主义者嘴边的中国/西方、我们/他们的二分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今人的二分思维受到近代种族主义、族群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影响,夷夏之间、他者与我们之间是绝对的敌我关系,毫无通约、融合之余地;而古代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不是固态化的种族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可打通、可转化的文化概念。夷夏之间,所区别的只是与天下价值相联系的文明之有无。天下是绝对的,
夷夏却是相对的;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但文明却可以学习和模仿。诚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在中国文化之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1 历史上有许多以夏变夷、同化蛮族的例子,同样也有以夷变夏、化胡为华的反向过程。汉人本身是农耕民族,而胡人多为草原民族,农耕中国和草原中国经过六朝、隋唐和元清的双向融合,许多胡人的文化已经渗透进华夏文化,比如佛教原来就是胡人的宗教;同时,汉族的血统里面也掺杂了众多蛮夷的成分,从服饰到起居,中原的汉族无不受到北方胡人的影响,比如汉人最初的习惯是席地而坐,后来喜欢上了胡人的马扎,从马扎发展为椅子,最后改变了自己的习惯。
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不衰,不是因为其封闭、狭窄,而是得益于其开放和包容,不断将外来的文明化为自身的传统,以天下主义的普世胸怀,只关心其价值之好坏,不问种族意义上的“我的”、“你的”,只要是“好的”,通通拿来将你我打通,融为一体,化为“我们的”文明。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只关注“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是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解决自我的文化认同;而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一国一族的普遍视野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中国的目标如果不是只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而是要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在今天要实现的不仅是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梦想,而且还应包括民族精神的世界转向。中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普遍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中华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应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是黑格尔所说的负有“世界精神”的世界民族,理应对世界承担责任,对传承“世界精神”承担责任,而这个“世界精神”,就是以普世价值形态出现的“新天下主义”。
二、去中心、去等级化的新普遍性
谈到天下主义,有些周边国家总会闻虎色变,担心随着中国的崛起,昔日那个骄傲自大、威震四方的中华帝国会起死回生,卷土重来。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缘由。传统的天下主义除了普世性价值之外,还有地理空间的含义,即以中原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天下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第一个是内圈,是皇帝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第二个是中圈,是帝国通过册封、羁縻和土司制度间接加以控制的边疆;第三个是由朝贡制度所形成的万邦来朝的国际等级秩序。从中心到边缘、从化内到化外,传统的天下主义想象和建构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蛮夷臣服于中央的三个同心圆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唐、宋、明的中原汉族王朝,还是辽、金、元、清的边疆民族王朝,其空间扩张的过程,既给周边地域和国家带来了高级的宗教和文明,同时也充满了暴力、征服和柔性奴役。
电话:010-80522028 传真:010-8052202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观音堂文化大道一期南花园村168号2号展厅25号
版权所有:北京思得乐图书有限公司 京ICP备20013354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131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1319号